

在西湖大學去年開學典禮上,徐益明講席教授鄧力說,自己當年在哈佛讀博時對導師產生了信任危機。因為當他在課題中遇到難題,導師竟無法給出答案,只能和他一起在失敗中學習。
今年開學典禮上,細胞生物學講席教授于洪濤說,做探路者不容易,但在西湖大學,有一群人和你們并肩戰斗。
他們在試圖告訴博士新生一件事:博士生與導師之間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學生對導師應該心存怎樣的預期,而導師對學生又應該抱有怎樣的期許?
傳道授業解惑,這是所有教師的共同職責,但對于博導和博士生這一對CP而言,又有一點不一樣。他們是自上而下的知識傳授,還是面對未知的共同探索?
在第37個教師節之際,西湖大學請三位資深教授從他們與各自第一位學生之間的故事說起,聊聊他們理想中的師生關系。
裴端卿:招學生首先跟他們交流價值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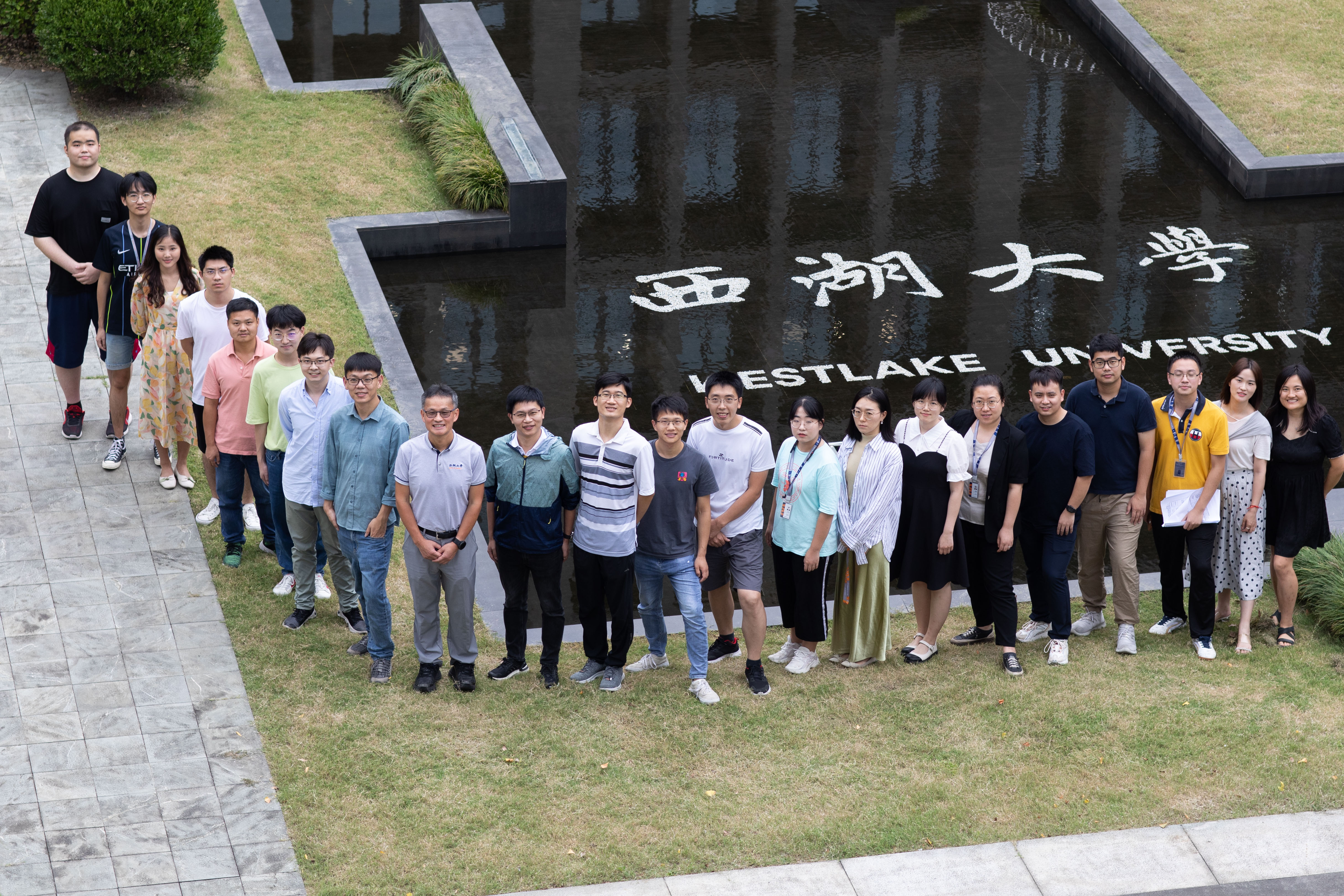
裴端卿和西湖大學團隊成員
裴端卿,再生生物學講席講授,1996年加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藥理系擔任助理教授,至今在大學任教25年。
我招收我人生中第一個學生是在1996年,那時我剛到明尼蘇達大學,有一位美國學生要來實驗室輪轉,我們系的學生不多,每年大概招收7個學生,但是我們系里有30多位faculty。
這就意味著不是每位老師每年都能招到學生,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一位學生能夠選你做導師,大家都會覺得你還不錯,對你的career發展有所幫助,也可以給senior faculty留下好印象。
面試了這個學生,我感覺也還不錯,于是就把他招進了實驗室。當時,我的實驗室里有一位技術員、一位博士后、一位博士生,加上我,一共4個人,是個很小規模的實驗室。
但是,后來這個學生又轉學離開了,我感到很mysterious,至今我都想搞清楚為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單獨帶學生,回想起來確實有些難,在他的身上花的時間不夠多,因為當時我剛當上助理教授,會逼著自己多做點實驗,多寫點文章。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還經常反省,有時候很認真地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往往結果不盡如人意,我這個例子不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但是可能對我們年輕教授有點借鑒作用。
一開始,在新的實驗室里我也沒想清楚要做些什么,都是自己摸索著來。后來,我再招學生的時候,我會比較強調價值觀。我教書已經有25年,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帶得比較成功的學生,首先會跟他們交流價值觀,為什么要做這個,為什么要進我的實驗室,我會先了解這些。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學生教會我的。
【理想的師生關系】
有時候,導師有導師的想法,學生有學生的想法,要搞清楚這個事情真正的內在本質是什么。我們做導師一定要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同時也要與時俱進,和學生一起成長。
王鴻飛:把愿意學習的人教得更好,才能真正成為一位好老師

2021年6月25號,王鴻飛與學生饒毅,及自己博士導師Kenneth Eisenthal的合影
王鴻飛,西湖大學理學院教授。1999年加入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后擔任博導約十余年。
我的第一個博士生是饒毅,是的,和西湖大學創校校董之一、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教授同名同姓。
饒毅是專科學校畢業的,后來在華中師范大學修了一個同等學歷的碩士,然后來考了中科院的博士生。我當時三十二歲,他比我只小大概不到兩歲,那時已經三十歲了。
雖然我那時候是第一次當博導,但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不能做得更好”——因為我有很多做博導的前輩可以作為榜樣,比如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期間的導師Kenneth Eisenthal——我很幸運,作為老師,他們的水平都很好。
其實我對饒毅的指導,就是和他一起討論具體的問題,包括每周一次的組會,會討論實驗室的進展、相關的文獻和下一步要做什么。而對于他,我的心態是很矛盾的,因為他不算一個“背景好”的博士生,在年齡、學歷、英文水平上都不怎么理想。一方面,我想鼓勵他,因為我判斷他在科研能力上沒有問題,我相信經過我們的訓練,他應該是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競爭的;但另一方面,萬一我鼓勵了半天,他還是不成功,那要怎么辦呢?
于是,我一直跟饒毅說,你要自己選擇你想做什么。其實最終成與不成,取決于他的決心,而他的決心很大,也很努力。
現在,他成為了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化學與生物化學系助理教授饒毅,他獨立做的工作非常漂亮,應該說從很大程度上,這些工作都是超過我的——而獨立做的研究工作好不好,才是我們衡量一個學生是否“好”的標準。前段時間在美國,我還專門去他的實驗室轉轉,想從他那邊“學點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我一開始做博導招到的學生,背景都不是特別的“好”,但這是對于年輕博導老師來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因為你只有把一個愿意學習的人教得更好,你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好的老師。有一條經驗分享,師生之間一定要多交流,討論具體的問題和細節,深入參與到他們的課題中去——當時饒毅這樣的學生不相信自己,我也不相信他們,所以我會天天跟他們討論問題,反而促進了他們的進步。
【理想的師生關系】
我希望博士生通過學習能夠學會怎樣做研究、怎么樣選擇問題、怎么把一個事情做到深入,這樣對他們才有好處。如果他們希望走捷徑的時候,我會告訴他們不可以,因為這種習慣會損害他們的未來。同時,每個學生都不一樣,導師要發揮他們的長處。
黃嘉興:指導學生是一項“不可重復”的實驗

黃嘉興和他的學生們
黃嘉興,材料學講席教授,2007年出任美國西北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助理教授,至今在大學任教14年。
我在西北大學帶的第一批博士生有兩位,其中一位是來自韓國的男生,他在LG工作過一段時間,然后選擇回到校園里讀博,所以年紀比我還長一歲。
也許是在工業界工作時養成的習慣,也許是因為服過兵役,這位男生做什么都很井井有條:實驗臺上的東西分類整理,收拾得無比干凈;實驗記錄也工工整整,尤其是數據整理,將實驗流程和數據都記錄得非常細致;每周一次的討論中,他可以拿出過去每一天的實驗日報……
相比之下,在課題的早期,我更偏愛在自由奔跑中尋找方向,并不拘泥于形式和細節。顯然,我很不適應這位同學的風格,甚至直接告訴他“沒必要這么做”,但后來的事實告訴我,每個學生身上都有閃光點,都有比導師厲害的那一面,作為導師要善于發現并尊重這一點。
當時我和他正在共同推進一個關于納米材料合成的課題,原本專注于一種化學合成的路徑和方法,我基于過往的經驗認為,可以暫時“放過”一些中間步驟,快速試錯。可是做到后面發現,我們的方法是可以從一個單一的產物延展到幾個系列的產物。一夜之間,過去一段時間的即時實驗數據變得非常重要,我很慶幸我的合作伙伴、也就是我的這位學生沒有放棄他的數據整理風格,是他身上的這個閃光點幫助我們高效地完成了課題。
后來,我們發了一篇很不錯的文章,將原本需要用幾篇文章解決的問題“濃縮”在一篇中講明白了。
這就是我和自己第一位學生之間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指導學生是一項“不可重復”的實驗,自己從前取得的經驗不能夠生搬硬套到下一位學生身上,最直接的辦法還是那句老話:因材施教。
【理想的師生關系】
隨著時間的推移,導師的經驗是在不斷增長的,但每一年進組的學生永遠是“萌新”,所以身為導師需要正視這一點,學會和新生重新站到同一條起跑線后面。
參考資料:https://www.westlake.edu.cn/news_events/westlakenews/UniversityNews/202109/t20210910_12510.shtml
聲明:化學加刊發或者轉載此文只是出于傳遞、分享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認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電話:18676881059,郵箱:gongjian@huaxueji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