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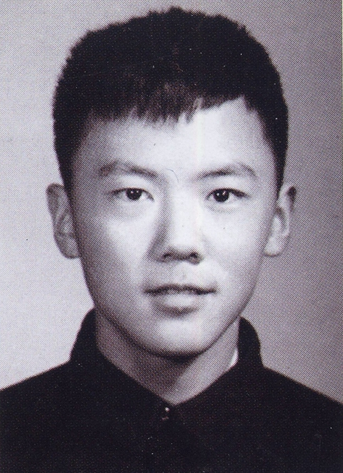
以今天標準來衡量,趙國屏無疑是一個“輸在起跑線上的人”:他小學上了7年,高中畢業到淮北農村“插隊落戶”十年,直到30歲時才考入大學,35歲留學美國竟然跟老師年紀相仿,知天命之年從研究微生物學、生物化學改行拓展我國新領域——基因組學……
然而這并不妨礙趙國屏成就卓然。一路走來,趙國屏56歲就獲評中國科學院院士,他和團隊的努力在人類疾病定位克隆上打破了西方科學家的壟斷。
他說自己不是最聰明的人,只是一直在努力,他用“勇擔重任、當仁不讓”寄語今天的青年一代。鑒于現在的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他呼吁父母應樹立榜樣并提供給孩子自由探索興趣的空間,而他的中學時代正是對此最好的注腳之一。
兒時興趣廣成就終身事業
1948年,趙國屏出生在上海一個技術官員家庭,父親趙祖康是我國著名的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專家,曾經擔任國民黨潰退時的上海代理市長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長。他是家中幼子,兄姊皆出于北大、清華、同濟等名校;從小在溫文嚴謹的環境中長大。
趙國屏自幼體弱多病,小學甚至讀了7年。為追趕進度,1962年,要強的男孩選擇了初高中五年制的位育中學。
這所由著名教育家李楚材創辦的學校,迄今為國家培養了兩院院士11人,著名大學校長26人。
趙國屏幼時父母曾經讓他去學過國畫、練過鋼琴;他自己也興趣廣泛,甚至在少年宮師從亞洲動畫開創者萬籟鳴的兄弟學皮影戲,但沒一項能夠堅持下來,“畫學了一個月,畫完梅花后便沒了興趣,鋼琴學了一陣子之后也就不去了。”
這個被父親批評沒有“恒心”的少年也曾想通過寫文章出名。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給雜志《少年文藝》投稿的情景:追夢少年站在郵筒前,四下顧盼,趁無人丟了信就跑。最終也因為沒有回音而放棄。
因為從小缺鈣,中學時代的趙國屏又瘦又矮,體育運動也成了一大遺憾。聽說收發電報也算運動競賽項目,特地報名參加了區工人體育館的培訓班,“一段時間后,教練就說我已經達到三級運動員的水平了”。
多年后回想,趙國屏感慨正是這一次次對于“前程”的嘗試,一個個興趣愛好的交替,讓他對世上萬物保持了一分特有的好奇心,直到與生物結緣。
“語文教材里介紹一位小學生,把番茄嫁接在土豆上面,結果上面長番茄,下面長土豆。”對于年少的趙國屏來說,無疑打開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門。
與生物有關的一切活動都成了趙國屏中學時代的課余愛好。3年自然災害,城里人也要想辦法搞吃的,這個市長家的孩子在院子里做嫁接,還養起了雞和兔子,“意識到這是生物體現出的經濟意義”。
上世紀60年代,趙國屏偶然在《科學畫報》上讀到一篇關于DNA雙螺旋結構發現后分子和細胞生物學發展的文章,其中提到病毒是介于生命和無生命之間的“生命體”,這讓小小年紀的趙國屏深為震撼、著迷。他下決心獻身生命科學研究,第一步,就是報考北大生物系。
要上大學,首先學好“數理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中物理老師。
在講到牛頓三大定律時,這位學校的二級教師帶來一疊油印教材,每人發一本,替換掉當時教育部特批(適用于五年制教學)的教科書,“他說那本書后面的內容是錯誤的,讓我們用他編的講義”。
當告別中學校園10年之久的趙國屏參加高考時,物理仍考了95分(百分制),“實際上是和這位老師的教育分不開的。他教的是經典的力學分析,讓學生避免了‘傳力’概念的誤導;從本質上對問題的認識正確了,方法是對的,題目就都能做對”。
面對今天中學教育里的“題海戰術”,趙國屏直言,學習需要掌握對問題的根本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靠題海練習里的“類比”和“經驗”。真正的創新在題海里是沒有的。
年輕人要有“當仁不讓”的豪情
個人的命運常常被時代所裹挾。
趙國屏遇上了“上山下鄉運動”的時代洪流,高中沒有正常讀完,班上同學陸續分在上海的工廠或周邊,然而他的“學生物”初衷無論如何都揮之不去,“想用生物知識改變農村”。
1969年1月,20歲的趙國屏自愿來到離家500多公里的安徽省蒙城縣,開始了近10年的知青插隊生涯。
他帶領插隊組同學和生產隊社員育種、搞試驗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窮村變為富饒之地,自己也從毛頭小伙兒成長為大隊書記。
下鄉伊始,知青學到的第一堂課,不是“階級斗爭”,而是“養活自己乃人生第一要務”。一年歉收,一人只分到40斤小麥。趙國屏等8個知青買了很多紅薯干,煮熟之后吃里面的心,皮給豬吃。
縣里文化局干部看到這一幕后感慨,“這樣家庭里出來的人能夠吃這樣的苦,將來一定是了不起的”。
1977年,恢復高考的喜訊傳來。趙國屏卻選擇了放棄高考。因為他放不下改造農村的心愿。
“你應該多學本領,做農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節,在生產隊長的勸說下,趙國屏清理完賬務,才回到上海復習備考。
而立之年,趙國屏終于跨入了復旦大學的校門。此時,他的年齡差不多是班上最小學生的一倍。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10年知青生活,魯迅的話鐫刻成了趙國屏一生的信仰。
如今帶學生,趙國屏勸誡他們要“勇擔重任,當仁不讓,就是當一件事很重要但是沒有人去做的時候,我能做我就必須去做;但是,這樣的事一定是難做的,所以要鍥而不舍地堅持做下去;同時,在做的過程中,認真學習,提高本領,把事情做成、做好”。
上個世紀末,中國提出參與全球人類基因組研究的兩個1%計劃,即完成人類基因組1%的序列測定和識別人類表達基因的1%,并特別關注人類疾病基因組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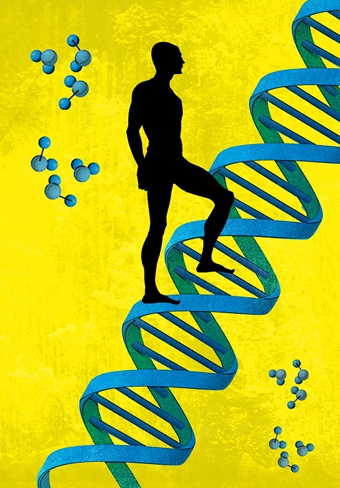
趙國屏受命帶領中科院團隊,參與這一重大科學研究項目。“人類基因”這4個字對已經50歲的他來說,聽到時的感覺,和所有的大學生是一樣的;所以,他只能邊學邊做,“我必須要去做,這太重要了”。
2003年4月中旬,中國和其他5個發達國家正式宣布:人類基因組序列草圖測定完成,一本人類遺傳信息的天書已經寫就。中國在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進展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非典”突發,全球恐慌。為揭秘“非典”流行過程中SARS冠狀病毒的進化規律,沒有任何項目經費的趙國屏和他的同事們,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奔赴疫區,通過調查研究,在Science、PNAS等權威雜志上發表了系列論文,為疾病防治提供了科學決策基礎,也讓那些認為中國科學家在非典領域研究失敗的評論戛然而止。
只追求個體的優秀難有偉大成就
多年來,在到各地的講學和交流中,趙國屏注意到一個現象,許多家長總把孩子的成長看成是學校的事情,“其實,好的家庭教育同樣重要”。
這個市長的小兒子即使看病誤了上學,父親用車送到學校時,也是在離校門遠遠的地方就要把他放下來。
自己數十年不用戴眼鏡則得益于父親的“幾不準”:躺著不準看書,吃飯不準看書,走路不準看書,坐在公共汽車上不準看書……
家里的燈光沒有那么亮,父親自己傍晚看書也一定要開臺燈,“家長要做很好的榜樣,小孩能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他無限感慨的是,在不少家庭,爸爸媽媽看電視,讓孩子自己在一旁做作業,小孩漸漸玩起游戲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當其他小學生在用很漂亮的鉛筆盒時,趙國屏也曾一度抱怨用比較舊的鉛筆盒,母親就教育他不要眼紅別人的東西,同時要樂于幫助成績不好的同學。家里的小院內,從小就是小伙伴的樂園,一起做作業,一起玩耍。甚至幾十年后,在普渡大學博士畢業答辯時,老師向同學們動情地提問:“你們在座的想想看,有誰沒有得到過國屏的幫助呢?”
歷盡滄桑后,趙國屏感恩這樣的家庭教育讓他受益太多,譬如這個剛上初中時與人說話就會臉紅的男孩漸漸學會了與人溝通交流,合作和分享;也學會了組織和管理。
在給復旦大學的新生作報告時,他勸誡學生們要學會在合作中成就大事業。回望自己的科研之路,單打獨斗效率太低,很多突破性的成果都是通過大團隊合作,通過跨學科、跨單位甚至是跨國家完成的,“希望同學們在今后的生活中,學會合作,創造合作,享受合作快樂”。
他用和自己在普渡大學共事10年的一位同學舉例,這位同學是若干重要信號轉導通路的發現者和鑒定者,曾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他在農村從小就是孩子王,這就是和人接觸中逐步形成的一種凝聚力”。
在趙國屏看來,凝聚力是一個人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在團隊形成過程中,必須有人具備或逐步形成這方面的能力;否則,團隊難以組成,也難以有效開展工作。
趙國屏曾面對不少“獨生子女”家庭出身、在“個人奮斗”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在他看來,今天的教育中,家庭或學校把孩子圈在一個個不同的小圈子里,一味地補課培優連軸轉,“僅僅努力追求個體的優秀,實際上很難取得偉大的成就”。
參考資料
聲明:化學加刊發或者轉載此文只是出于傳遞、分享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認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電話:18676881059,郵箱:gongjian@huaxueji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