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中和,1930年8月生,江蘇凓陽人,我國著名細胞生物學家。1950-1951年在清華大學學習,1951-1956年留學蘇聯,畢業于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1959 -1961年在前蘇聯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進修。1984-1986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學系做訪問教授。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院士。現為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翟中和教授在我國較早建立細胞超微結構技術,首次研制成鴨瘟細胞疫苗,在動物病毒復制與細胞結構關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進行核骨架—核纖層—中間纖維體系、非細胞體系核重建、細胞凋亡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創新成果,被國內外所引用。先后在國內外發表論文280余篇,專著15部。他主編的《細胞生物學》被評為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是國內同類教材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已發行50余萬冊。
艱苦環境鑄就良好素質
翟中和,1930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蘇省溧陽與宜興交界的一個農村水鄉。8歲的時候,他的母親因病去世,慈愛善良的祖母擔起了撫養他的責任。翟中和7歲開始在當地的一所非常偏僻而簡陋的鄉間初級小學接受啟蒙教育。一位嚴厲的先生講授小學1-4年級所有的課程,每個年級先生只能講15分鐘,其余的時間就要靠自學。艱苦的環境,使他從小就養成了獨立學習與獨立思考的習慣,對他今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初小四年級,剛滿10歲的翟中和,就要到離家六里遠的一所完全小學去讀書了。那時正值抗日戰爭,四處兵荒馬亂,家中的情況日漸困窘。他早晨只能喝一點粥,很早就要出發去學校。初冬的江南水鄉,稻田在濕冷的空氣中微微透出光芒。天空陰霾而低沉,常常大雨伴著驟風,如注而下。10歲的翟中和光著腳丫,把油紙傘的傘柄頂在自己的肚子上,踩著泥濘的小路,逆風走向離家六里遠的學校。
初中的三年,時局依然動蕩不安,翟中和轉了三次學才讀完初中。1946年,他考入了江蘇省立溧陽中學。高中時的翟中和除了對文學有興趣,對其他學科并沒有太明顯的喜惡,各科成績也比較均衡。他給自己的評價是:“缺乏抽象邏輯思維的能力,推導公式的能力差,數理類或工程類不是我能力所及的專業。”在考大學前,他仔細考量了自己的優勢和特點,并結合所處的環境,作出了大學進入生物學系學習的重要決定。當時要填報高考志愿表時,翟中和開始填寫了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他的同班同學無意中看到他的志愿表,便問他為何不報考清華大學?他想了想,覺得也可以,就涂掉了原來的志愿,重新填報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就這樣,翟中和考入了清華大學。
翟中和的少年時代沒有受到良好而系統的教育,但艱苦的條件鍛煉了他自學自律的能力,培養了他承受巨大困難的心理素質和毅力。他一生中從不怨天尤人,從無懷才不遇之悲,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充滿希望,勇往直前。
1950年,翟中和從江蘇農村來到北京,進入了清華大學,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清華園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和神秘。“我第一次看到了實驗室和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了顯微鏡,第一次使用自來水和電燈……”他在清華大學生物系的一年級就先后聆聽了著名生物學家陳幀、趙以炳和沈同等教授開設的普通生物學課程,李繼侗教授講授的植物學以及張青蓮教授講授的普通化學。這些知名的老師把復雜的課程講得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內容把這位來自農村、穿著大褂的學生引入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1951年,翟中和通過了教育部選派蘇聯留學生的考試,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被派往蘇聯學習。臨行前,周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他們。翟中和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劉少奇講過的話:“新中國剛建立,現在國家還很窮,打仗、打天下是我們老一輩的責任,你們的責任就是建設祖國,所以在蘇聯學習要盡量考5分。”
翟中和被派往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生物系學習,他分外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到了蘇聯一切都為了保證學業,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他的成績單一目了然:除了一門歷史唯物主義考了4分,其他的44門課程全部考了5分。要知道他到蘇聯的時候,是完全不懂俄語的!這個成績的取得,必然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到北大訪問,翟中和給他當翻譯,這位官員表揚他說:“你的口音很純正!”

早年的翟中和先生。
歷經磨難,癡心不改
1956年,26歲的翟中和帶著優秀畢業生的榮譽從列寧格勒大學畢業了。因為1952年院系調整,當時的清華大學生物系與北大動物學、植物學兩系及燕京大學生物學系合并為新的北大生物學系。北大生物系系主任張景鉞和副系主任張龍翔希望翟中和可以來北大工作,征求他的意見時,翟中和很老實地回答說:“這不由我決定,要服從組織分配,組織分配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就這樣,翟中和被分配在了北京大學生物系任教,先后隨同李汝祺教授和沈同教授做助教,從事遺傳學和放射生物學的研究。
1959年,翟中和再次被派往蘇聯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進修,主攻電子顯微鏡技術和生物電子顯微學,師從弗蘭克院士和別里科夫斯卡婭通訊院士。別里科夫斯卡婭曾經是美國遺傳學家穆勒的學生和助手,翟中和評價她“是一位真正的科學家”。當時她已年逾六十,但精力過人,對這位中國弟子言傳身教,悉心指導,這些都對翟中和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翟中和在后來的回憶中認為“這段時間是我科學研究工作的真正入門”。應用電子顯微鏡研究細胞超微結構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技術,這一選擇使翟中和受益匪淺,以后的數十年里他和他的學生、助手應用電子顯微鏡與其他技術相結合,在細胞生物學方面做了很多系統而有特色的工作,成為我國生物電子顯微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
1961年,翟中和回到北京大學,次年任講師。在當時的中國,科研條件極其簡陋,加之政治運動不斷,很多科學研究工作停滯不前,要做一點工作是很困難的。然而,翟中和最可貴的地方恰恰在于其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下并沒有放棄科學研究,反而以一種飽滿向上的積極態度,因地制宜,在艱苦情況下創造條件,堅持做實驗、做研究。
1969年,翟中和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干校勞動鍛煉。盡管感覺不公平,翟中和卻仍然能夠認真對待自己在干校里的“工作”——養豬和種水稻。他把豬養得又肥又壯;他作為班長的一個種稻班,水稻年年豐產,被稱為“水稻豐產班”。因為表現突出,他被評選為江西省勞動先進分子,還曾到井岡山參加省里的先進分子表彰大會。
1973年,翟中和回到了北京。北京大學生物學系已經開始逐步恢復日常教學和科研工作,但工作條件和設備仍然很差。結合當時的特定條件,翟中和完全憑借對科研的熱情和執著追求,歷經十年的努力,在家禽、家畜治病病毒的分離、鑒定和疫苗研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義、有實踐價值的工作,并“在畜牧獸醫界小有名氣”。在進行應用性科研工作的同時,翟中和對病毒細胞關系這一基礎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利用電子顯微鏡等手段,對多種致病病毒在細胞內的復制、裝配及其與細胞超微結構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發表了六十余篇論文,組成一個有特色、有活力、有創造的科研集體,并為后來成立的細胞生物學專業打下了基礎。
重學問,淡名利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真正迎來了“科學的春天”。而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隨著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生物科學在國際上的發展異常迅猛。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翟中和深感自己原來研究的超微結構形態學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需要在科研中引入分子生物學技術。基于這樣的考慮,1985年至1986年,已經是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翟中和,在年屆55歲時第三次遠赴海外求知。這次他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生物學系佩曼(S.Penman)教授的實驗室做訪問教授,從事細胞核骨架及其與基因表達關系的研究。翟中和意識到我國的生命科學發展水平已經遠遠落后于國外,“只有不斷調整方向與步伐才能跟上形勢。選擇先進的、有理論意義的又適合我們實際情況的科研課題成為我們繼續前進的關鍵問題。”
在美國的學習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半,翟中和格外珍惜這個機會,恨不能延長每天24個小時,爭分奪秒地工作。忘我的工作也讓翟中和付出了健康的代價,長期的飲食失調,使他患上了糖尿病。翟中和只能暫時依靠一些藥物緩解病情,同時堅持在實驗室里工作,就這樣一直堅持到回國。即使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翟中和在美國的一年半時間里仍然發表了3篇論文。“我并不聰明,我最大的優勢就是勤奮。我相信勤能補拙。”這是翟中和認為自己能在專業領域取得成績最重要的原因。
從美國回國以后,經過較長的分析與考慮,翟中和決定選擇“細胞核骨架—核纖層中間纖維體系”的研究作為主攻方向之一。核骨架與核纖層是否存在當時有爭議,然而這一問題的研究對解釋細胞核與染色體的結構與功能會產生新的概念。歷經翟中和與他的五、六屆研究生十多年的艱苦奮戰,這一領域的研究真正與世界接軌了,此后他們的研究工作步入系統性,發表五十多篇論文,其中多篇論文被國外重復引用。
1991年,翟中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這之后,他除了科學研究,每天更多了很多事務性的工作。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掛了一幅字,上書:“重學問,淡名利”六個大字,提醒自己以做學問為重中之重。這時的翟中和仍然堅持指導學生,包括在實驗室做論文的本科生的工作,他都要過問,并親自幫他們修改論文、聽預答辯。

翟中和集體照。
從1978年北京大學建立細胞生物學專業至今,在翟中和的帶領下,從建立學科、開設細胞生物學課程,到建立博士點、成立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再到現在建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將北大的細胞生物學從無到有,建設為現在中國高校中實力最強的學科。
翟中和對于科學的發展有著卓越的預見能力和堅定的執著信念,對科學上的新東西有極大的興趣,而且不怕付出任何代價。即使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仍然堅持研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在有限的條件下做一些工作。科學的春天到來后,他又有新的想法,編寫教材、建設學科,抓科學研究。
早在上世紀70年代翟中和就強調當老師必須做研究,只有搞好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務教學。在當時很多老師不重視實驗研究,但翟中和特別重視將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實驗教學結合起來。把教學工作做好,并最終把教學經驗積累起來,寫幾本能夠影響一兩代人的教科書,這是翟中和的一個理想,也是他的教學理念。
這個想法在上世紀80年代得以實施,1995年翟中和編寫了《細胞生物學》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了9萬多冊,如今,《細胞生物學》已經再版了三次,平均每年銷售5萬冊,有270個學校的專業和相關專業學生都在使用這本教材,是國內同類書籍中影響最大的,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細胞生物學》還獲得了200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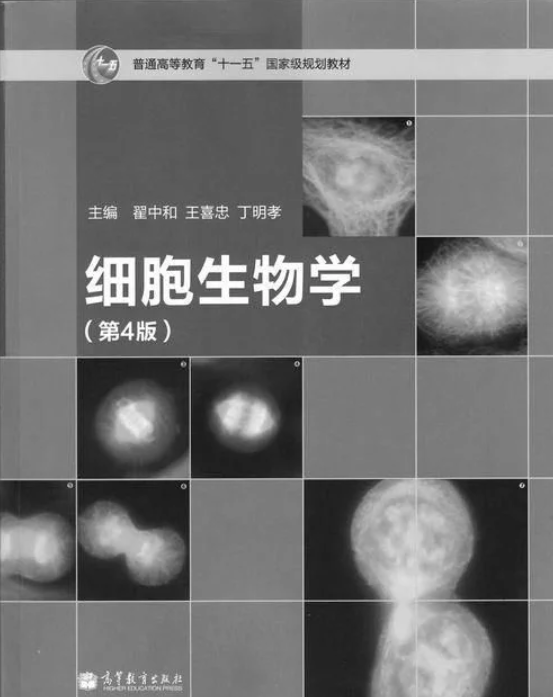
翟中和教授主持編寫的《細胞生物學》教科書第四版。
翟中和的許多工作都圍繞著北大細胞生物學科的發展和建設。他作為學科帶頭人,無疑是這個學科的核心。他不僅專注于自己的研究,更把大量的心血放在了學院、學科的整體發展上。翟中和還很重視對青年科研力量的培養,他常常教導自己的學生,提醒他們為年輕人的發展考慮,多注意對年輕人的培養,給還需要提高的老師多些支持、多些建議、多些幫助,讓他們盡快成長起來。
124,我們共同的名字
2000年,70歲的翟中和仍孜孜不倦地工作著,一面為學校講課、扶持地方院校的學科建設,另一方面,他當時擔任著中國科學院學部常委、教育部生物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并擔任“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等的評審專家,其他的學術兼職更是難以計數。每天的繁忙讓人總是以為他還是個年輕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席完博士生答辯會后,走下樓梯時突然感覺天旋地轉,同時不停地嘔吐。被同事送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無法清楚流利地講話,無法看清東西。經診斷,確診為腦血栓。這之后的兩年,他又因同樣的病癥先后住院兩次。
翟中和現在已經不能親自參加科研工作了,但他培養起來的學生現在“已經不是一支隊伍,而是一個陣營了”。翟中和1978年開始招收第一批碩士研究生,1985年成為博士生導師,三十多年來共指導了80余名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現在他的學生中有10位在北大做教授、副教授,10多位在國內其他院校或研究所做教授、副教授。還有10多位在國外做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及雜志總編輯。還有幾位任公司總經理或廠長。
這些學生團結在翟中和的身邊。2007年,細胞生物學實驗室被評為全國優秀集體,這個集體有個代號叫做“124”,124是他們朝夕相處、做研究工作共同使用的老生物樓的大實驗室。一批批的學生從這里走出去,在海外他們寫信回來總是深情地“問候124,懷念124”。這些學生從他身上學到的不僅是科學知識,更多的是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教育學生的理念。(作者單位:北京大學)

1996年8月2日,學生們在實驗室為翟中和院士(前排右二)慶祝生日。
參考資料
聲明:化學加刊發或者轉載此文只是出于傳遞、分享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認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電話:18676881059,郵箱:gongjian@huaxueji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