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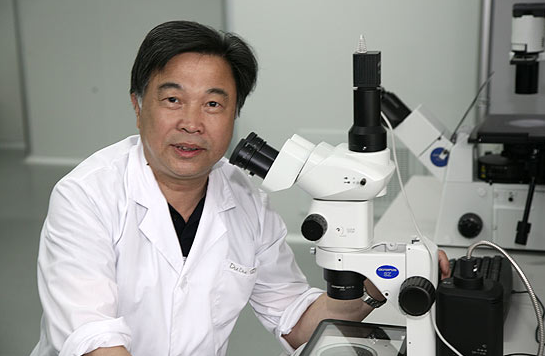
對(duì)大自然愛(ài)恨交織的感悟,讓楊煥明產(chǎn)生了探索生命的動(dòng)力,走上了科學(xué)之路
直到現(xiàn)在,楊煥明還能清晰流利地背出英語(yǔ)書(shū)里幾乎所有的課文及后面的補(bǔ)充閱讀和英文詩(shī)歌
至今,楊煥明仍每天讀30篇以上的文獻(xiàn)資料,他把這看作“戲讀”,如游戲一般
有人說(shuō)水鄉(xiāng)的孩子愛(ài)水,山里的孩子愛(ài)山,海邊的孩子愛(ài)海。但是,基因組學(xué)家楊煥明院士卻對(duì)家鄉(xiāng)的山水海“愛(ài)之深、恨之切”。
楊煥明生在浙江溫州樂(lè)清的一個(gè)小山村,近山、傍水、臨海。干旱時(shí)節(jié),土地龜裂,顆粒無(wú)收,求雨不得而“恨天”;洪水之后,河水泛濫,險(xiǎn)些讓兒時(shí)的他淹死而“恨水”;窮人“爬山當(dāng)棉襖”而“恨山”,漁家“腳踏船板半條命”而“恨海”。
每到周日,他被父母逼到海邊捉魚(yú)蟹,腰帶上系著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米餅。下海灘時(shí),他看到去撈小魚(yú)蝦的地方在水平線上腳已發(fā)軟,頭上是炎炎烈日,腳下是齊膝深的、踩不到底的泥巴。回來(lái)時(shí)看岸邊猶如天邊,緊隨身后的是咆哮著的洶涌潮水。
爬不盡的陡峭的山路,貧瘠的黃土,山地里撿不盡的石頭,鋤頭迸出的火花。一放學(xué)就被媽媽派去割草、砍柴,至今右手上一道橫跨三指的刀疤清晰可見(jiàn)。
“哪個(gè)農(nóng)村孩子,不希望‘不勞而獲’呢?”小時(shí)候的楊煥明恨不得秧苗能一夜長(zhǎng)成稻谷,水稻能像茭白那么高,谷子能像蠶豆那么大。
而恰恰是這種對(duì)大自然愛(ài)恨交織的感悟,讓楊煥明產(chǎn)生了探索生命的動(dòng)力,走上了科學(xué)之路。
多年后,昔日懷揣“拔苗助長(zhǎng)”夢(mèng)的楊煥明帶領(lǐng)他的團(tuán)隊(duì),在世界上首次利用全基因組“霰彈法”策略完成了水稻這一大型植物基因組的測(cè)序和分析,由我國(guó)科學(xué)家獨(dú)立完成的超級(jí)雜交水稻父本秈稻“9311”基因組“工作框架圖”,揭開(kāi)了其高產(chǎn)、優(yōu)質(zhì)、美味背后的奧秘。
“只有吃苦,才懂得珍惜”
楊煥明至今記得,小時(shí)候父親幾次把他領(lǐng)到村里一位清代舉人的老宅邊,指著門(mén)前那一對(duì)石柱對(duì)他說(shuō):“以前窮人的孩子只能靠科舉,現(xiàn)在只有讀書(shū)考上大學(xué)!”
楊煥明曾莫名其妙地厭學(xué)、逃課,跟媽媽說(shuō)學(xué)校有活動(dòng)不用上學(xué),出去打架、用彈弓打死人家的雞,做了壞事也不承認(rèn)。
“是金老師把我拉了回來(lái)。”外校轉(zhuǎn)來(lái)的金老師聽(tīng)說(shuō)他曾讀書(shū)很好,堅(jiān)信他不是個(gè)壞孩子,一直鼓勵(lì)他。
“過(guò)去沒(méi)有條件讀書(shū),現(xiàn)在的孩子有條件不想讀書(shū),所以在他們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一定要吃苦,歐美的很多家長(zhǎng)還把孩子送去‘魔鬼訓(xùn)練營(yíng)’”,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楊煥明說(shuō),只有吃苦,才能懂得珍惜,才會(huì)更加熱愛(ài)學(xué)習(xí)。
小學(xué)五年級(jí)時(shí),楊煥明已經(jīng)把所有的演義小說(shuō)都看遍了,《封神榜》、《東周列國(guó)志》、《三國(guó)演義》、《楊家將》……今天的他掰起手指,一一歷數(shù)。憑借大量閱讀,楊煥明的作文成績(jī)一直非常好,老師要學(xué)生自己用毛筆謄抄貼在墻上的優(yōu)秀作文,幾乎都是他的“專(zhuān)利”。
同樣讓他很有成就感的是,這個(gè)班里個(gè)子最小的男生成了學(xué)校里的“孩子王”,身后總跟著一群大孩子,“只有我的故事能吸引他們,才能讓他們心服口服,從來(lái)沒(méi)有人欺負(fù)過(guò)我。”
其后,楊煥明順利考上了當(dāng)時(shí)縣里唯一的中學(xué)——樂(lè)清中學(xué)。
校園里學(xué)風(fēng)很好,剛進(jìn)校時(shí),楊煥明甚至有點(diǎn)自卑。有一次作文才得了64分,為此他偷偷哭過(guò)鼻子。
但這個(gè)自尊心很強(qiáng)的男孩很快追了上來(lái),成績(jī)?nèi)嗟谝唬之?dāng)上了班長(zhǎng)。青澀的記憶里,還有這樣的片段——在學(xué)校的運(yùn)動(dòng)會(huì)長(zhǎng)跑中,身材瘦小的楊煥明堅(jiān)持到底,獲得了“風(fēng)格獎(jiǎng)”。也只有這樣才能彌補(bǔ)體育分的不及格,他才能年年評(píng)上三好生。
楊煥明說(shuō),這是一段心無(wú)旁騖的校園生活,“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就是一個(gè)夢(mèng),我的夢(mèng)就是考上北大清華”。
然而,這樣的中學(xué)生活只維持了一年半,伴隨著全國(guó)“上山下鄉(xiāng)”運(yùn)動(dòng)戛然而止。
多年后,楊煥明在一篇隨筆里曾這樣喟嘆:“下次到北京,我一定要帶上一包煙去行賄看門(mén)的老爺爺,讓我再進(jìn)一次北大,再坐在圖書(shū)館前那片草地上,再做一次那永遠(yuǎn)不可能圓的北大夢(mèng)。”
“不要讓自己的夢(mèng)想睡去”
和正在熱播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并無(wú)二致,楊煥明回鄉(xiāng)的生活很辛苦,早起、挑水、干農(nóng)活。很多鄉(xiāng)親眼中,這個(gè)有股子吃苦勁的少年以后肯定能做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連他的母親也相信了。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我一定不會(huì)在這里一直待下去。”
在那個(gè)“讀書(shū)無(wú)用論”盛行的年代,楊煥明把看書(shū)當(dāng)成是自己最大的享受,高爾基說(shuō)“我撲在書(shū)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而他更愿意說(shuō)的是“無(wú)用才讀書(shū)”。
“書(shū)都被燒了,只剩下3本我偷偷藏著的英語(yǔ)書(shū)”,直到現(xiàn)在,楊煥明還能清晰流利地背出英語(yǔ)書(shū)里幾乎所有的課文及后面的補(bǔ)充閱讀,還有所有的英文詩(shī)歌。在別人看來(lái),那段色調(diào)暗淡時(shí)光的夜晚只剩下疲憊,但是對(duì)于楊煥明而言,在夜晚的煤油燈下讀書(shū)是一種享受。
多年以后,在英國(guó)劍橋郊外舉行了“國(guó)際人類(lèi)基因組計(jì)劃”會(huì)議。會(huì)上,就是否接受中國(guó)參與進(jìn)行了答辯。楊煥明據(jù)理力爭(zhēng)、激情答辯,爭(zhēng)取到了1%的任務(wù)份額,其還算流利但帶有濃重中國(guó)南方口音的英語(yǔ)表達(dá),讓與會(huì)者印象深刻。
在做民辦教師、罐頭廠臨時(shí)工的間隙,楊煥明四處找書(shū),和人換書(shū),每看完一本就立刻和別人交換。那段時(shí)間楊煥明自學(xué)完了初中高中的英語(yǔ)、數(shù)學(xué)、物理全部課程,也把縣城能找到的書(shū)全都讀遍了。
“沒(méi)有所謂的好書(shū)壞書(shū),那時(shí)只要能找到的都是可讀之書(shū)。”從《激光》、《射流》到《十萬(wàn)個(gè)為什么》,從《法蘭西內(nèi)戰(zhàn)》到《哥達(dá)綱領(lǐng)批判》,從《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yàn)批判主義》到《國(guó)家與革命》,還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只要楊煥明能找到的,他都讀過(guò)。
在楊煥明的少年朋友和青年工友記憶深處,他永遠(yuǎn)是這樣一個(gè)形象:挎著一個(gè)黃書(shū)包,里面總是放著要讀的書(shū)。
他驕傲地自嘲當(dāng)年是個(gè)“自虐狂”,為磨煉自己的意志常年洗冷水澡;而除了拼命學(xué)習(xí),楊煥明還有一套自己的學(xué)習(xí)方法,周密的學(xué)習(xí)計(jì)劃,然后一絲不茍地執(zhí)行。記憶中,這些似乎源自“福爾摩斯”叢書(shū)中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
當(dāng)年與他曾同住一室的工友至今感慨,“他這個(gè)人說(shuō)好每天背30個(gè)英語(yǔ)單詞,就一定做到!”
他說(shuō)自己經(jīng)歷的時(shí)代讀書(shū)是不得已的,為了生活、為了家庭、為了夢(mèng)想,但是卻沒(méi)有條件學(xué)習(xí),“現(xiàn)在我們不能強(qiáng)迫,要放手,一定要讓他們覺(jué)得學(xué)習(xí)與玩游戲一樣有趣。”
“能愛(ài)上科學(xué)的人都是幸運(yùn)的人”
在愛(ài)上生物學(xué)之前,楊煥明最先被物理學(xué)和化學(xué)折服。
龍骨水車(chē)的樣子至今總浮現(xiàn)在他腦海里:父輩們頭頂烈日,腳下一刻不停地踩著輪盤(pán),拯救干枯的秧苗。后來(lái),龍骨水車(chē)被替代,柴油機(jī)讓鄉(xiāng)村的寧?kù)o一去不返。
物理能用機(jī)器代替人更快更好地工作,但是化學(xué)卻能做人不能做的事情。
楊煥明的家鄉(xiāng)蟲(chóng)災(zāi)嚴(yán)重,農(nóng)民們用農(nóng)藥噴灑來(lái)滅蟲(chóng),楊煥明目睹了“科學(xué)的威力”,也與父兄們一同慶賀“科學(xué)神藥”的來(lái)臨。但是很快,不幸也來(lái)臨了,害蟲(chóng)沒(méi)有滅絕,河田里的魚(yú)蝦卻消失了,更不幸的是,當(dāng)魚(yú)蝦再次出現(xiàn)的時(shí)候,孩子們卻被告知魚(yú)蝦再也不能吃了。
物理和化學(xué)的“威力”讓楊煥明震驚,也真正讓他開(kāi)始愛(ài)上自然、生命。
對(duì)生物的最初感受,是鄰居用沾滿(mǎn)泥巴的手遞來(lái)的一節(jié)藕。這塊從泥巴中挖出的、橫切面布滿(mǎn)大大小小巧妙排列孔洞的植物,令楊煥明感到神奇,“這是我第一次為神奇的大自然所造就的生物之美所感嘆!”
更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則是回鄉(xiāng)期間一段在縣釀造廠學(xué)農(nóng)業(yè)微生物和在縣罐頭廠做蘑菇師傅的經(jīng)歷。
釀造廠總技術(shù)員萬(wàn)老師成為楊煥明生命中的“貴人”——她給了楊煥明閱讀大學(xué)生物教材的機(jī)會(huì),還教給他微生物的基礎(chǔ)知識(shí)。
1975年,楊煥明走進(jìn)了杭州大學(xué)的校門(mén),就讀他喜歡的生物系。從此他生命科學(xué)研究的序幕正式拉開(kāi)。
至今,楊煥明仍保持每天讀30篇以上的文獻(xiàn)資料,他把每天看書(shū)、看文獻(xiàn)當(dāng)作是“戲讀”,如游戲一般。科學(xué)對(duì)于他來(lái)說(shuō)是輕松而快樂(lè)的,他從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樂(lè)趣。
楊煥明經(jīng)常到中學(xué)跟孩子們交流,用形象幽默的語(yǔ)言解讀生命的奧秘,讓他們感受科學(xué)的樂(lè)趣。
近年來(lái)與年輕一代的交流和觀察中,他遺憾地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學(xué)校學(xué)習(xí)成績(jī)好的都不去做科研了,而是選擇賺錢(qián)的行業(yè),“對(duì)科學(xué)有興趣的小孩越來(lái)越少”。
今天的孩子心中想的都是如何從競(jìng)爭(zhēng)中勝出,而楊煥明覺(jué)得,“自己愛(ài)上科學(xué),真是一輩子的幸運(yùn)!”
參考資料
聲明:化學(xué)加刊發(fā)或者轉(zhuǎn)載此文只是出于傳遞、分享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認(rèn)同其觀點(diǎn)或證實(shí)其描述。若有來(lái)源標(biāo)注錯(cuò)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quán)益,請(qǐng)作者持權(quán)屬證明與本網(wǎng)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更正、刪除,謝謝。 電話:18676881059,郵箱:gongjian@huaxuejia.cn